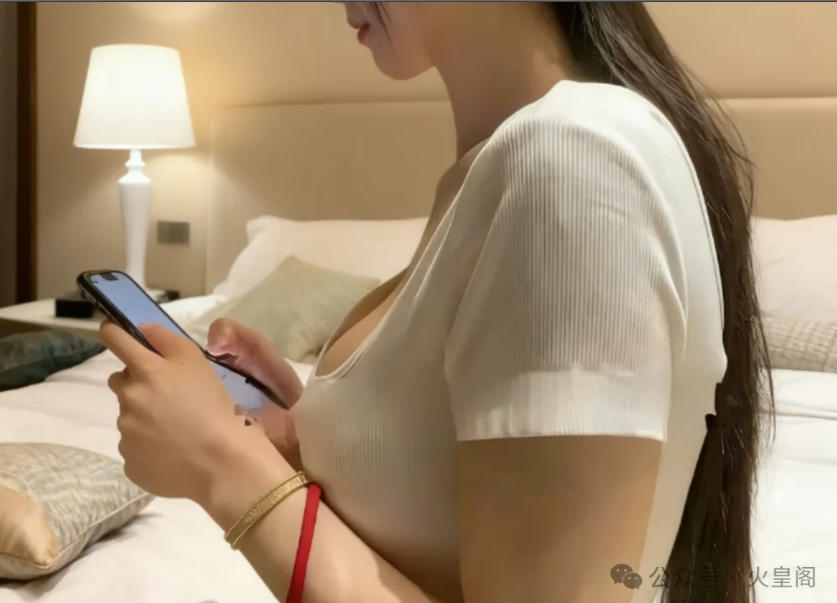我握着手机,听着漫长的等待音,心脏一下下撞击着胸腔。终于,电话被接起,那边传来一个平静无波的声音,正是那天在街角遇见的道士。
“我记得你。”道士打断我,语气没有任何意外,“你遇到你想问的事了。”
“他……他跟我说了‘望月鳝’。”我几乎是颤抖着,把那个关于采阴补阳、化骨丹、采收元阳的诡异传说复述了一遍。每说一个字,那晚的恐惧和浑身发烫的触感就清晰一分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,随即响起一声几不可闻的轻笑。
“望月鳝?这个比喻真恰当。姑娘,你还不明白吗?他口中的‘望月鳝’,说的就是你们这些月光族自己。”
我愣住了,下意识地重复:“……我们?”
“不错。”道士的声音带着一种冰冷的洞彻,“所谓‘望月’,看似汲取月华,实则自身精元也在不断消耗,如同那月光下的工薪之人,每月领着薪水,看似光亮,转头便交了房租水电,还了车贷房贷、信用卡花呗,周而复始,到手空空,一身精气神,皆为他物所采。此谓之‘白领’——就是白领一场,为人作嫁,与那望月之鳝何异?”
我握着电话,指尖冰凉。
这番话像一把冰冷的钥匙,猝不及防地捅进了我习以为常的生活锁孔里。
房间里死寂一片。我缓缓滑坐在地,耳边只剩下道士那句冰冷的话在回荡——
望月鳝,月光族,白领。
我生活的恐怖寓言,原来早就写好了。
我瘫坐在地,浑身冰凉。道士的话像淬了冰的针,扎进我每一寸赖以生存的认知里。
原来我日夜奔忙,不过是一场为人作嫁的精致献祭。
“所以……我就没救了吗?”我的声音嘶哑,带着最后一点不甘。
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,似乎在看什么。随后,他平静地开口,语气里竟似多了一丝极微弱的、可以称之为“缓和”的东西。
“你的‘病’,不在那姓秦的身上,也不在那虚妄的传说里。你的病,在于你自身的‘气血’已弱,神光已黯,才让外邪有了可乘之机。大厦将倾,你只顾着咒骂风雨,为何不先想想,为何独独是你这栋楼,如此摇摇欲坠?”
这话像一只手,把我从泥潭里猛地拽起一寸。

“那我……该怎么办?”
“街角,‘火皇阁’。”道士的声音清晰传来,“去那里,找一个叫当归的人。告诉他,你需要一味 ‘定神砂’。”
“当归?定神砂?”我喃喃重复,这听起来比“望月鳝”更像一个神话。
“人名‘当归’,是告诉你,该让流散的精气神,回归本位了。药名‘定神’,是稳住你惊惶不定的心神。”他的解释依然冷静,却像在黑暗中,为我划亮了一根火柴。“至于那到底是什么,你去了便知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信不信由你。”道士打断我,语气复归那古井无波的淡漠,“医不叩门,道不轻传。路,指给你了。”
说完,电话便被挂断,只剩下一串忙音。
我握着手机,良久,终于支撑着站起身。窗外,城市的霓虹依旧喧嚣,那无数盏灯下,又有多少只像我一样的“望月鳝”?
我不知道“火皇阁”和“当归”是不是另一个更精致的陷阱。
但我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。
我拿起外套和手机,推门走进了夜色里。这一次,我要主动走向那传说之中。